编者按:本文节选自郝志东教授旧文《什么叫“农民”:一个华北农村的个案研究》的文献回顾部分。介绍了农民的定义、农民与市民的不同,以及从传统农民到现代农民的转变。详实并清晰地展现了几十年来农民的政治和生活的基本处境。本文的后半部分更精彩,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即将上市的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书《知识分子与农村发展》。
农民的定义
正如秦晖所指出的,“什么是农民”这个问题,在困惑着众多的、古今中外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等。不过,对当代中国农民的定义,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似乎变得容易了一些。于是,总的说来,有狭义的农民与广义的农民之分。狭义的农民指职业上的农民,即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不过有时人们也把从事渔业、牧业、林业等的人们看作农民。广义的农民则指户口不在城市(鎭)的人,即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即使你已经去了城市做工、经商,定居在城市,只要你没有拿到城市户口,你就是农民。不过,你就是拿到了城市户口,别人也可以说你还没有脱离“农民习气”。所以,秦晖说,农民“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
这一点和韦伯所定义的社会地位在意义上是相通的。韦伯说,所谓社会地位是指一些人主要是由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所受教育程度不同而被他人看重的程度也不同的这样一种情况。而你被人看重,和你有更多的权利、收入,及其它获利的机会是有关系的。韦伯还讲,社会地位既可以是阶级的原因(即地位高,阶级也高),也可以阶级的结果(即由于阶级高,所以地位高),不过它也可以和阶级没有关系。阶级是由市场机会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1949年以前乡下的地主和贫农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但是从社会地位上讲,他们都是农民。上个世纪末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形成的新阶级,尽管阶级不同,但由于户口都在农村,所以从社会地位上讲,也都是农民。
总之,在当今的中国,只要你从事和农业有关的行业,尤其是你持有农村户口,那么你就是农民。前者是狭义的农民,后者是广义的农民。正如我们在下面要讨论的,即使在2014年国务院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之后,农民问题还会继续存在很长时间。
下面,我们将分析这个农民阶层的几个内涵,包括农民和市民的不同,农民的分化和职业化,以及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化。这些都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看到农民定义的实质内容。我们先来看农民和市民的社会地位到底有哪些不同。
农民和市民的不同
关于农民和市民的不同,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看得出来:1、进城的农民工被歧视的情况;2、城乡差别;3、户籍制度。这些问题告诉我们,农民是二等公民。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1、进城的农民工被歧视的情况
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农民进城做工,实质上已经变成了工人,但他们的户口在农村,身份仍然是农民,故被称为“农民工”。他们在城里的经历,可以凸现出他们的社会地位。很多调查都显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其它进城讨生活的农民在城市里受到歧视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首先,几个社会声望调查都表明,声望最低的通常是与农民工有关的职业。如对北京市民的一项社会声望调查发现,在100个职业中,排在最后十位的是乡镇企业工人、进城经商的农民、单位保安人员、进城做工的农民、搬运工、保姆、包工头、废品收购人员、人力车夫、传达室人员等。
其次,农民工的低社会声望,又和他(她)们在城市被歧视联系在一起。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如何被歧视,已经有很多研究。总起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是劳动福利权益的被剥夺,如他们超时工作,每天达十多个小时,且得不到劳动法规定的加班工资;他们的工资常被拖欠;他们得不到应得的劳动保护,致使职业病、工伤事故频繁发生;他们的生活条件通常很差(常住工棚、空间狭小、潮湿拥挤、蚊蝇滋生、饮食简单、营养单调),等等。
第二,是加在他们身上的诸多制度性限制。比如农民工在城里做工、居住,需办证件多种。2001年的北京市即要求他们办《流动人口证》、《暂住证》、《就业证》、《健康证》、《婚育证》、《职业资格证书》等。办齐这些证件,除了花去不少精力之外,还要付出400-500元。
除此之外,城市还限制农民工可以从事的行业和工种。比如2001年的南京市便限制他们只能做诸如建筑、环卫、矿井、装卸、搬运、泥瓦等劳动量大、技术含量低、挣钱少的工作,而限制他们做清洁工、营销员、厨工等,并禁止他们做商店营业员、宾馆服务员、电工、驾驶员等。北京市在2000年将限制使用农民工的行业增加到103个。他们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最险及城市人最不愿干的“五最”行业。
2003年中共中央出台政策,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也有城市开始取消《暂住证》。但政策真正得到实施,而且能够大面积铺开,恐怕还有相当的难度。以上这两点可以说是制度性的歧视。这些问题,尽管这些年来得到一些改善,户籍制度也在改革当中,但是如果没有彻底的、根本的改革,恐怕还是无法解决问题。

第三,个体性和制度性歧视的混合。一些田野调查提供了不少“城里人经常欺负人”的案例。
有些可能是个人行为,但这种现象太多了之后,实际上已经可以被看作是制度性的歧视。比如黑恶势力、地痞流氓对农民工的欺压、打工妹被拐卖、蹂躏;汽车售票员看你是乡下人,就抬高票价;职业中介把你骗到人家里做活,活完之后说你做得不好,把你赶走;工商局的人掀外地来城市摆摊、卖菜的人的桌子、砸他们的东西;城管罚款,开票就罚得多,不开就罚得少;你即使有《暂住证》,但派出所可以说你没有固定职业,如果不罚款,就让你去干半个月的苦力活,之后将你遣送回乡。但是因为在城里挣钱,即使被罚,也比农村多,所以人们还是会再回来。
总之,农民工劳动福利权益的被剥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限制,以及他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感受到的其它种种个人性和制度性的歧视,都只能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农民在城市里是二等公民。他们所从事职业的社会声望最低,也就不太奇怪了。当然我们可以说,或许工人所从事的职业本来声望就是靠后的,城市工、农民工皆然。但是城市工人的声望却是在“农民”工人的声望之上的。下节讨论的城乡差别,会进一步凸现这个问题。
2、城乡差别与不平等
城乡差别是一个老话题了。在马克思那时就有了。在中国急速发展的今天,那些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如何减少乃至消灭城乡差距,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本节对城乡差距的讨论只限于凸现农民和市民的区别,进而了解到底什么叫农民。农民和市民在韦伯指出的生活方式、教育机会等问题上到底有哪些不同,以至于他们被认为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是处在二等公民的位置上?我们将只简单介绍政治、社会、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问题上的不平等。
政治上的不平等。早在1953年,中央政府就已经规定,在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8倍。也就是说,农村每一选民的实际选举权是城市每一选民的实际选举权的1/8;在选举省、县人民代表时,农村选民的选举权则分别是城市选举权的1/5和1/4”。1995年选举法修改之后,之前的8倍现在被减少到4倍。这项政治不平等条款直到2010年才被人大通过修改选举法而取消。当然其在法律上的平等并不等于实际上的平等。一般的老百姓仍然无权乃是不争的事实。
社会保障上的不平等。同样,早在1951年和1953年,中央政府就规定了城市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福利,比如公费医疗、丧葬抚恤、退休金、养老金、产假、住房等种种待遇,而农民的生老病死却全部要靠他们自己负责。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后,并没有多大变化。在1999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中,城市人均413元,而农村则只有14元,相差29.5倍。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城市已经做到“应保尽保”,但农村则近几年才开始,而且力度也较城市为小。2007年中央出台了新政策,“重点保障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等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但由于杯水车薪,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巨大差距看来并不会缩小太多。
医疗卫生、生活环境上的不平等。张晓山先生的研究指出,之前占中国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换句话说,全中国另外30%的人口占了其80%的卫生资源。世界银行的调查也显示了类似的分配比例。在城镇化得到大力发展的今天,国家在城镇的投资还是大大多于其在乡村的投资。之间的不平等,对革命了近一个世纪的共产党人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新的合作医疗制度在2003年出台之后,国家与地方政府分别承担了一部分买医疗保险的本金,但农民的负担,由于收入不多的原因,还是较重。另外因为不是所有农民都参加了合作医疗,而且保险公司承担的医疗费用比例较小,于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仍然是常见现象。再加上农村医疗条件的简陋,医疗水平的参差不齐,国家投入的力度不够等,城市和农村的不平等还是显而易见的。
在生活环境上,城市的敞口厕所已经逐渐在消失,而一些地区的农村的敞口厕所却没有多大改变。由于没有垃圾收集站等设施,农民或把垃圾堆在村前屋后,或倒入山沟水塘。这些都导致了局部空气污浊,蚊蝇滋生,时刻都在损害着农民的健康。这和在城市中国家和市政府对环境卫生的重视、投资并使其得到大幅改善的状况是无法相比的。
李景汉等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河北定县做社会调查后在其报告中讲,“公众卫生及个人卫生习惯尚谈不到,三房(厨房、卧房、茅房)情况,一塌糊涂”。定县调查距今已近一个世纪,如果说农村在厨房与卧房方面,在改革开放以来,改善还不错的话,茅房的情况则改善不大。整体公共卫生状况,如上所言,也改善不大。
在私人卫生方面,也正如田翠琴和齐心2001年在他们的河北调查中所发现的,“家里没有洗澡设备的经济欠发达村的占79.7%、经济中度发达村的占59.2%、经济发达村的占23.2%。”而且即使有洗澡设备,多数人家也是用所谓的“热水袋”,只能在夏天用,冬季只能洗一、二次澡。另一个调查发现,在山西运城农村95%的农民家庭没有牙刷,而毛巾在相当多的农户中少有用途的区分。这些情况在城市中都是罕见的。由此可见公共和私人卫生在农村之缺乏。
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在城市,几乎100%的学龄儿童均可入学,在农村,每年尚有100万儿童不能入学。1985年城市小学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入初中,农村则只有64%。在城市,由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从1985年的40%提高到1999年的55.4%,农村则从22.3%下降到18.6%。1989年高校录取的新生,来自农村的占44%,城市的则占56%。换句话说,城市人民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是农民的4.9倍。下面这一段话可以形象地告诉我们城乡在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
北京有花费3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小学,而贵州、甘肃乃至于距北京数十公里内的农村还有很多“危险校舍”;城市的“中产阶级”或“白领”们每年要花费数千元【注:现在动辄上万元了】去培养其子女的“综合素质”,而农村那些尚未实现温饱的家长们要为筹集数十元的学杂费而一筹莫展;城里重点小学或“试验小学”的教师们常会出国度假旅游,而广大农村里的教师有的还领不全他们每月的薪水……
当然,以上情况近年来有所改变,如农村教师基本已由民办转为公办,欠薪的事情已较少听到,国家也明令取消了农村孩子们的学杂费。但城乡教育机会、办学条件等方面的巨大悬殊,仍然还在复制着教育的不平等。除非国家改变“财权上交、事权下放”的财事权不对称状态,否则农村教育的不平等仍然会继续。即使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的子弟,也不可以像城里人的子弟那样上学,他(她)们需要在那里“借读”,要看人家的眼色行事,通常还要多交各种费用。
3、户籍制度的改革
以上我们分析的农村务工人员在城市受到的歧视以及城乡的差距,都和户籍制度有关。换句话说,农村户口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农村和城市在生活方式、条件、受教育的机会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代表着这些差距的农民身份使得他们在进城后受到了种种限制与歧视,于是就有了农民和市民地位的不同。在同一个国家里,有的人是一等公民,另一些人是二等公民。于是,杜润生、秦晖、李昌平等人就认为农民问题是人权问题,公民权问题,是国民待遇问题。
当然,国家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中央出台了多项支持农村发展的政策,包括免去农业税,取消对农民工就业的种种限制等。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的意见,提出要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行政区分,无论城乡,人们都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意见要求各地“促进有能力的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定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但是由于这些工作的艰难性、由于实现市民待遇所需要的庞大资金,注定了上述的“有序实现”和“稳定推进”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本书对知识分子与农村发展的讨论,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农民实现公民待遇的过程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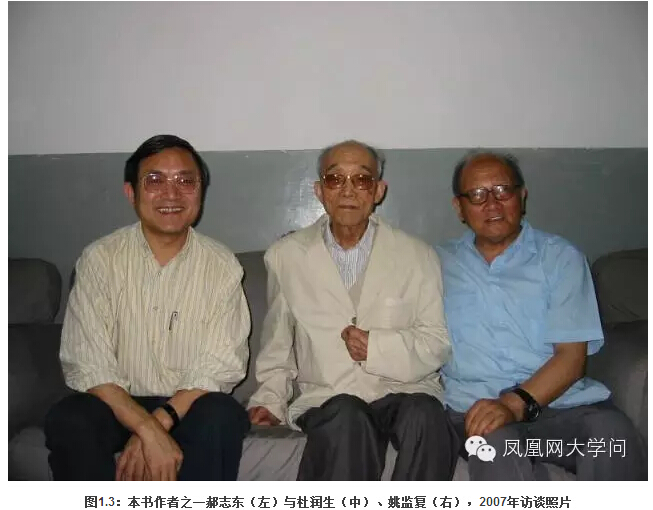
所以在一个长时间内,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仍然会存在。我们上面讲到的那些不平等仍然会存在。其实,不少学者多年前就呼吁解决“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问题。陆学艺在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就已经提案,指出当时的户籍制度在严重地阻碍着城乡的发展,城乡人民在户口面前应该人人平等。农民和市民的不平等仍然在继续定义着城乡居民。和古代中国一样,户口在城里的是“国人”,户口在城外的是“野人”。这么多年之后,才刚出台一个解决户口问题和差别待遇的“意见”,可见改革之艰难。
在国家还没有能力或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别问题、解决农民地位低下的问题的时候,农村和农民自身却没有停止自己的发展。于是,什么叫农民,就不单单是由城乡关系、以户口来界定,还要由农民自己的发展来界定。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些发展,包括农民的分化和职业化等从传统农民到现代农民转化的四个方面。
从传统农民到现代农民的转变
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的过程,是农民的“角色、身份、组织状态、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转变的过程。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种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呢?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又如何进一步定义农民呢?我们想从四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看它们在城乡差别之外如何界定农民的身份。这些问题包括:1、个人发展;2、农民的分化与职业化;3、村民自治;4、政治、经济组织;和5、生活条件。
1、个人的自由发展
无论是马克思,韦伯,还是迪尔凯姆,所有主要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都谈到了现代社会中阻碍个人发展的种种问题。比如马克思谈到了人的“异化”,工人不能够控制生产过程以及产品,资本家也掉入“钱坑”,不能自拔。韦伯谈到“笼子”效应,即现代人陷入了追求效益、速度、成果还是追求平等、自由、感情的两难境地。迪尔凯姆则谈到如何从“机械团结”迈向“有机团结”的现代化过程,即人们所从事的不应该是“被强迫的分工”,而应该是“自然分工”。所有这些社会学家都关心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发展是否自由这个问题。现代化以后人们不一定就完全自由,但是,传统社会中人的自由一定是比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为少。
中国农村的发展,自由和不自由经常交替存在,但却基本上是从较少自由到较多的自由发展的过程,即逐渐开始发现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提高自我的过程。比如人们通常认为,合作社、人民公社时期是最不自由的时期。社员们只能“听喝”,“社主任叫干啥就干啥”,他们认为自己在为社里“扛大活(当长工)”,社员个人活动被控制过死,积极性得不到发挥。“有队长一人操心就行了,我们操心也无用”。“干部乱派工,社员头发懵,干活一窝蜂,好坏分不清”。“出工人等人,做工人看人,收工人撵人,评工人打人。”但据学者研究,在管制人们自由方面,从两周到秦汉时期的“官公社”与1950年代的“人民公社”相比豪不逊色。
不过,改革开放之后,农民基本上有了择业的自由。即使农民工在城市受到歧视,但他们还是有了离开农村的自由。离开之后又怎样,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徐勇、徐增阳就谈到了农民在流动中促进了自己“公民人格”的形成和公民文化的成长,因为他们的政治认知水平提高了,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了,对传统和权威的认识和评价也和以前不同了。所以我们基本可以讲,在个人的自由发展方面,传统农民正在向现代农民,或者说向现代公民迈进。
2、农民的分化与职业化
农民的分化在这里是指阶级的分化,而农民的职业化则指农民身份的专业化。前者是农民的政治身份,后者是农民的职业身份。阶级问题是一个连马克思都没有为我们讲得很清楚的问题。不过,正如我们前面引述的韦伯所说,它和市场有关系,和人们在市场上的机会有关系。这一点和马克思没有矛盾。一方面是拥有生产资料,并雇佣他人来为自己生产幷创造利润的人,另一方面是那些被雇佣的人。在这样一种生产关系中,前者拥有支配后者的权利,而后者却通常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是因为后者,不像前者,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还没有真正地组织起来,所以还没有形成真正的阶级。这一点,在前面对农民工的讨论中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尽管还没有形成真正的阶级,农村的阶层却已经分化,在向阶级的道路上走。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
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估计,在土改前,即约1949年前,中国农村的地主和富农约占10%(其中4%地主,6%富农),中农约占20%,而贫雇农则占70%。在土改后阶级分化的结果显示有众多的贫雇农变成了中农,即出现了“中农化”现象。二者之比现在是中农60%,贫雇农30%,地主富农未变。在山西省的5个典型村庄,中农已占农户总数的88%。在老区土地改革后的几年期间,甚至有新富农出现。把农村的阶级分化描述为三种似乎失之于简单。比如,贫农和雇农就有相同也有不同。李景汉就描述了二、三十年代河北定县农村的农工情况,包括长工、月工与日工,农工、女工与童工,以及他们的工作内容、工资报酬、饮食待遇等。不过他主要描述的是长工的情况。
于是,1950年的农村人口就又被分为13个阶级和阶层,包括1、地主;2、资本家;3、开明士绅;4、富农;5、中农;6、知识分子;7、自由职业者;8、宗教职业者;9、小手工业者;10、小商小贩;11、贫农;12、工人、手工工人;13、贫民、游民。在土改前后阶级阶层分化的复杂则可见一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农村阶级阶层开始了新一轮的分化。陆学艺把它描述为八个身份:1)农业劳动者阶层(从1989年的55%-57%下降为1999年的48%-50%,下面每两组数字同为1989和1999之比);2)农民工阶层(从24%下降为16%-18%);3)雇工阶层(从4%上升为16%-17%);4)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从1.5%-2%上升为2.5%);5)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从5%上升为6%-7%);6)私营企业主阶层(从0.1%-0.2%上升为0.4%-0.6%);7)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从3%下降为1.5%);8)农村管理者阶层(从6%上升为7%)。
比较土改前后和改革之后农村阶级分化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第一,以前农村的地主、富农、开明士绅、资本家已经没有了,取代他们地位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他们现在是农村的有钱阶级,而且掌握着农村的权力。第二,以前的中农和贫农,现在是农业劳动者阶层。第三,以前有长工、短工等农工,现在有雇工,而且人数在增加。第四,以前有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现在有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第五,以前有农村知识分子,现在也有。第六,宗教职业者以前有,现在也有,只是不多就是了。如果说以上第一组人是农村的上层阶级,统治阶级,第四、五、六组人是农村的中产阶级,那么第二、三组人则是农村的劳动阶级。所以说,农村的阶级分化已经恢复了土改前后的样子,尽管上述第一组人和以前的构成有所不同。我们应该再次重申,尽管我们称他们为阶级,他们还只是走在成为真正的阶级的路上。说他们现在仍然是“阶层”比较恰当。
如果说农民的分化是指阶级和阶层的分化,那么农民的职业化,则指阶层分化的另一方面,即职业身份的确定。换句话说,在阶层分化之后,人们的职业趋向稳定。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谈到职业分化的时候,就指出江村的四种职业:1、农业;2、专门职业(包括纺丝工人,零售商,航船,及手工业与服务行业,其中有木匠、裁缝、理发匠、泥水匠、接生婆、和尚等);3、渔业;和4、无业。这种职业化,在土改之后,基本终止,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又重新开始并加深。比如,乡村的管理者趋向公务员化,他们的专业就是农村管理。企业主在职业化之后,已经不再务农。他们已经不是农民,尽管他们还在农村。个体工商户在职业化后变成了工商业者,主要工作也已经不是务农。农村的打工者实质上已经变成工人。当然,以上这些人都可能还有一小片地可以耕种。那些从事种植业的人似乎职业化的速度较慢,因为他们还是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主,还没有形成规模经营。但是农村职业化的趋向似乎会迫使这些农民进行职业化的转型。将来只有少数人经营农业,而多数人则转向其它行业,正如我们看到的雇工数目的增加一样。
3、村民自治
这是和个人的自由发展、农民的分化和职业化有着密切关联的一个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是以集权专治和缺乏自治为特点的。源于北宋、沿袭到清代的“保甲制”以及国民政府的“连坐法”便起到了严密控制人民的作用。不过尽管如此,乡里社会仍然有自治的因素存在。元代农村有“村社”组织,由社长主管。元代北方还有像“锄社”这样的农民组织。黄宗智则认为,尽管专治的“皇权中国”更适用于描述华北,但是“士绅社会”或“地主制”则更适用于描述长江三角洲。换句话说,自治的成分,后者多于前者。但是应该说各地多少都有一些。清末民初之后,政府在各地掀起了自治运动,于是,不光在南方,北方也多由地主、豪强负责起自治来。山西阎锡山的村本政治,基本就是这样的情况。
从抗日战争时起,中共的组织就在广大的乡村开始扎根,最后在村一级建立了党支部,国民政府时期的自治彻底结束,中央集权再次登上历史舞台。不过,在四十几年之后的1987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之后,农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村民自治体制还是慢慢建立起来了。“海选”制、“两票”制、“组合竞选”制等方法也陆续被运用。而民主正是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决定性的标志。换句话说,尽管农村选举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指选、排选、假选、贿选、党支部和村委会关系难以理顺(选上来的只是“二把手”)、黑恶势力掌权等问题,但是,村民自治这一基本体制现在看来应该不会再返回到公社体制上面去了,而且民主制度本身还有可能蔓延到其它领域、其它层级。从这一点上讲,农民的现代化已经超越了市民。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管理者的自由。
4、政治、经济组织
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经济组织,代表农民分化和职业化之后不同群体的利益,通过政治协商,解决村里面临的问题,那么村民自治是很难真正达到它的目的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也就往往变成了一句空话。但是,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组织状况如何呢?情况似乎不太乐观。
正如沈延生、张守礼指出的,目前农村的自治力量有以下几类:1)经济能人,或新乡绅;2)传统的宗族势力;3)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势力;4)宗教势力。他们同时指出,如果仅靠这几种势力,中国农村就没有现代化,而是回到了一个世纪前的中国。村民自治,还需要有各种非政府的现代社区组织,如农会、农业合作组织、扶贫济困的民间慈善组织等。那么农村这些现代社区组织情况如何呢?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还处在萌芽甚至空白状态。就是在发展比较好的地方,涉及到的农户也很有限。比如北京市在2002年有各类合作社2,030家,入社农户34.2万户,但仅占全市农户总数的28%。1998年全国有农技协会11.56万,加入农户620万,仅占全国农户总数的2%。
在政治方面,农民组织就更难出台了。中国各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全国性组织,唯独农民没有,这里当然也包括农民工。那些没有在任何组织之内的大多数农民如何维护自己的政治权益,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些农民维权、依法抗争组织,也在逐渐兴起。它们用上访、宣传、阻收、逼退、静坐示威等方式维权。但是效果很难讲。一来它们通常是不合法的、未在政府部门注册的组织。二来是政府也不给它们注册。所以它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很小。农民工的反抗,也仅限在怠工(或破坏机器设备)、逃避(跳槽)、罢工等方式。官方的工会如何将农民工包括在内,并能够真正为他们维权,还是一个未解的问题。
无论是经济组织,还是政治组织,在中国农村的发展都有很多的阻力,因为当权者认为它们可能成为“压力集团”,与党和政府唱“对台戏”。如果成立了,就要么全盘否定,要么置之不理,希望它们能够自生自灭。多少年来,杜润生、温铁军、于建嵘等专家、学者都呼吁应该允许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但至今收效甚微。所以说,在组织意义上讲,中国的多数农民离现代化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那么在生活条件上如何呢?
5、生活条件
在这方面,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李景汉研究过的“三房”情况,除了茅房之外,厨房和卧房已经在走向现代化。现代化有许多指标,包括恩格尔系数、第三产业的结构、人均居住面积、每万人口律师数,以及另外一些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协调发展状况的指标。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了其中的一些方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在提到城市化战略问题时,指出了城市化的三种模式:小城鎭化、中等城市模式、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模式。他认为还应该有第四种模式,就是“乡村生活的城市化”。也就是说,这里的乡村生活在劳动方式、衣食住行、文化生活、闲暇生活等方面,和城市生活幷没有太大的不同。这也正是我想说的生活条件的现代化问题。这也是本文想重点探讨的现代化的一部分。那么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江苏省江阴市华西郊村,如果说在其它现代化条件上,我们很难说如何的话,至少在生活条件上,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标准。他们的生活条件已经比很多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都好。下面我们把华西郊村的“八有八不”全面抄录下来,以方便我们对现代化生活标准的描述:
1.小有教(从幼儿园到中学集体提供学费,考上大学、自学成才有奖)
2.老有靠(老农民享受退休保养金)
3.房有包(统一规划别墅式民居,集体承包建筑)
4.病有报(社员生病,足额报销,工伤全报)
5.购有商(购买商品不用出村)
6.玩有场(有闭路电视、影剧院、卡拉OK歌舞厅、农民公园)
7.餐有供(上班职工午餐免费)
8.行有车(已定购捷达车250辆,其中50辆已进村)
1.吃粮不用挑(集体送粮到户)
2.吃水不用吊(有自来水厂)
3.煮饭不用草(家家装管道液化气)
4.便桶不用倒(户户有抽水马桶)
5.洗澡不用烧(热水管道通各家)
6.通讯不用跑(户户有电话)
7.冷热不用愁(冬有暖气夏有空调)
8.雨天不用伞(长廊环绕全村)
但是像华西郊村这样的村子,全国并没有几个,生活条件全部达到这个标准在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还不可能。有病足额报销、抽水马桶、冷暖空调、热水管道等极难达到。不过,“八有八不”中的另外一些标准,如小学免费、闭路电视、购物商店、自来水、电话、空调等还是有可能达到,有些农村也已经不同程度地达到了。
从上述的五个方面:个人的自由发展、农民的分化和职业化、村民自治、政治和经济组织化的程度以及生活条件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化的程度。从这些方面讲,如果农民真正实现了现代化,他们也就实现了公民化。我们之前讨论的那些明显的城乡差别也就不复存在了。那时也就无所谓农民还是市民了,因为之间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不过,在当前,上面讲到的这些问题仍然在定义着农民这一社会群体。
在文献回顾这一部分,我们主要讨论了农民和市民的差别,以及农民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从文献回顾来看,中国农民基本可以被定义为“社会地位低于市民、在个人自由、分化与职业化、政治自治、组织化、生活条件等方面的现代化程度参差不齐的这样一个社会群体”。本研究试图通过对一个乡村的调查,来看以上对农民的定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在这个村的农民身上,从而检验这个定义的可用性,同时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农民这个社会群体的未来。
作者简介:郝志东,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获社会学博士,澳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凤凰网大学问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